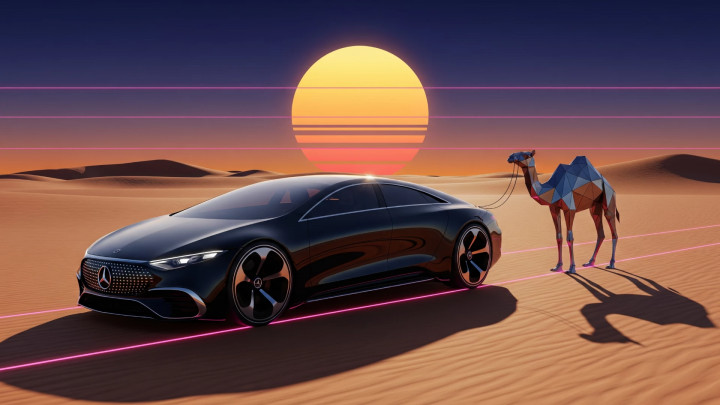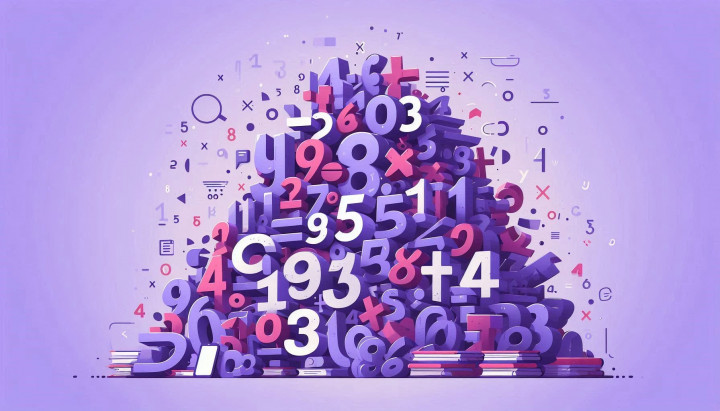“我的祖父骑骆驼,我的父亲也骑骆驼,我开奔驰,我儿子开路虎,他儿子也会开路虎,但他的孙子将不得不再次骑上骆驼……”
“这是为什么?”
“艰难困苦造就强者。强者创造安逸时光。安逸时光造就弱者。弱者带来艰难困苦。很多人不会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培养能够创造和战斗的人——而不仅仅是消费。”
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迪拜的现代设计师谢赫·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所说(尽管其确切来源和原文措辞难以考证,但其表达的情感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愿景完美契合),它精准地捕捉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悖论之一。这句话出自一位亲眼见证一个沙漠采珠港口转变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都市之一的领导人之口。但这仅仅是一个戏剧性的警告,还是一条支配文明兴衰的铁律?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的视角来探讨这一观点。
循环的剖析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模型的逻辑。这个概念描绘了一个四阶段的、自我延续的循环:
- 艰难困苦 → 强者:物资匮乏、为生存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以及外部威胁,锻造出坚韧不拔、足智多谋、纪律严明且积极进取的一代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成功意味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是能够从无到有创造价值和稳定的“战士”。
- 强者 → 美好时代:这代坚强的人通过辛勤工作、牺牲和明智的决策,建立了一个繁荣的社会。他们建立起和平、安全和经济福祉,让后代得以在其中成长。
- 美好时代 → 弱者:出生在已然繁荣的时代里的人,往往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从未为之奋斗过,因此不理解其真正价值。舒适使他们自满,持续的安全感削弱了他们的风险偏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更可能消费前辈的财富,而不是在其基础上继续创造。他们是将繁荣视为一种定数,是用来享受而非再创造的人。
- 弱者 → 艰难困苦:当新的、严峻的挑战出现时(经济危机、战争、自然灾害),这代毫无准备、沾沾自喜的人无法有效应对。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缺乏必要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最终导致他们所继承的体系衰落和崩溃。循环闭合,艰难困苦的时代再次来临。
历史的回响:我们在哪里见过这种模式?
这个模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推演。历史上充满了与此循环惊人相似的例子。
- 罗马帝国的衰落:这是个经典的案例。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是由坚韧的农兵公民(“强者”)建立的。通过征服,他们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与和平(“罗马和平”——即“美好时代”)。数百年后,罗马精英生活在颓废和奢华之中,而城市大众则靠免费的谷物和宏大的娱乐(“面包和马戏”)来安抚。社会失去了其内在力量,由“弱者”领导的帝国无法抵御内部危机和外部蛮族的入侵。当然,其衰落的原因更为复杂——经济、军事和行政因素都起了作用——但这个模式依然清晰可辨。
- 伊本·赫勒敦与沙漠法则:或许没有人比14世纪的阿拉伯博学家伊本·赫勒敦更科学地阐述过这个循环了。他引入了“阿萨比亚”(asabiyyah)的概念,意指群体凝聚力、社会团结和共同目标感。他认为,游牧的沙漠部落(生活在“艰难困苦”中)拥有极强的“阿萨比亚”。这使他们能够征服一个已经软化的城市文明。然而,一旦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的“阿萨比亚”在几代人之内就会被侵蚀,然后他们又会被一个新的、强大的群体所征服。
周期性思想的传统
在这句名言的智慧背后,是一种审视历史重复性和文明生命周期的悠久哲学传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得出结论,历史并非直线前进。
-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他20世纪早期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中,将文化比作会出生、成熟、衰老和死亡的生命有机体。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其最后的衰落阶段,其特征是物质主义和精神空虚。
-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用他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来解释文明的命运。崛起的关键是成功应对挑战,而当一个文明的创造性精英失去了活力,无法再应对新问题时,衰落就会发生。
- 现代“历史动力学”之父彼得·图尔钦使用数学模型来研究历史。他的理论表明,长期的和平(“美好时代”)会导致精英过剩和社会不平等加剧,最终引发内部冲突和政治动荡(“艰难困苦”)。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试图用数据来捕捉文明的周期性变化。例如,彼得·图尔钦和他的同事们在他们的“历史动力学”模型中,分析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人口、精英过剩和内部冲突的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和平与繁荣时期,精英阶层的数量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机会的增长速度,导致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并最终引发危机。
然而,其他指标则描绘了一幅更为微妙的图景。史蒂芬·平克的研究表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暴力发生率、战争死亡人数、儿童死亡率和极端贫困等长期趋势已急剧下降。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凸显出,历史并非遵循单一模式。虽然有些社会可能确实在富足时代步履蹒跚,但人类整体上仍在学习和进步。这或许表明,“循环”并非一个完美的圆圈——也许它更像一个螺旋。
循环能否被打破?——反方论点
自然,历史的循环观也有其批评者,尤其是在那些相信人类能够进行集体学习和进步的人当中。许多人认为,历史并非一个决定论的循环。
- 启蒙运动与线性进步观:像孔多塞这样的18世纪思想家认为,通过人类理性和科学,人类正不断向一个更美好、更发达的状态前进。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是一个向上的轨迹,而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 现代史学的怀疑态度: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对宏大且包罗万象的理论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类模型过度简化了复杂的现实,忽略了偶然性的作用,并低估了人类在塑造自身命运中的能动性。
- 史蒂芬·平克与基于事实的乐观主义:这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用数据论证,尽管存在悲观的预测,但从许多指标(暴力、贫困、疾病)来看,世界正在变得更美好。这种观点表明,我们有能力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有意识地避免衰落。
问题悬而未决
回到谢赫·拉希德的名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力量不在于科学上的精确性,而在于其隐喻的深度。文明的命运或许并非一个以铁的逻辑运行、不可阻挡的循环。但是,这个警告——安逸会使我们软化,繁荣会让我们忘记那些创造了繁荣本身的美德(毅力、谦逊、牺牲)——在今天依然像以往一样有效。
或许,在21世纪相对和平与富足的环境中,我们能问自己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是历史上最安逸时代的子民,是“美好时代”的后代。我们能否打破这个模式?我们能否利用我们的繁荣,不是变得更软弱,而是变得更智慧、准备更充分?
还是说,历史的车轮真的无法阻挡地转动——我们的孙辈将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骑骆驼?或许,人类将首次成功打破这个循环,将繁荣转化为持久的智慧,而非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