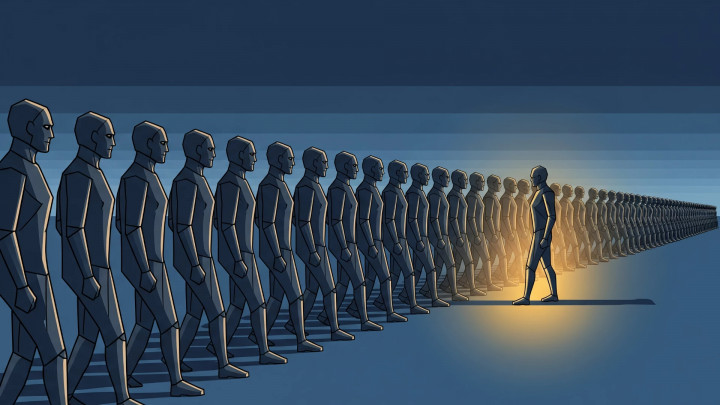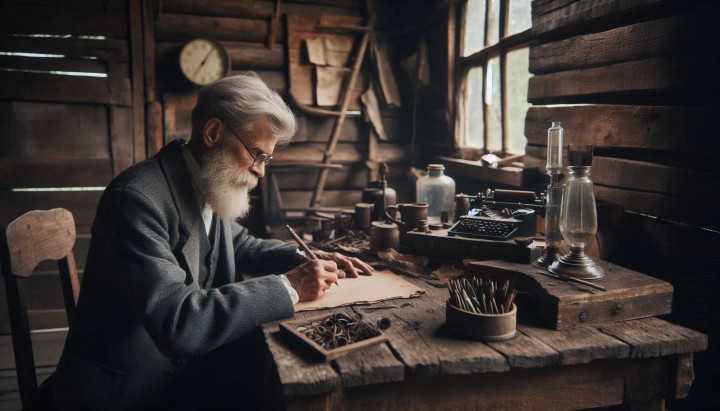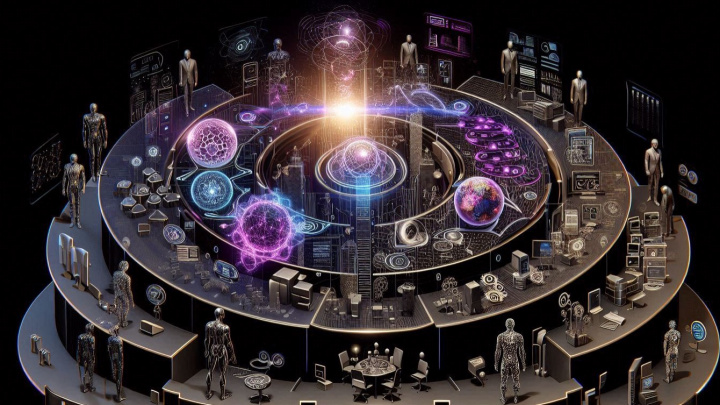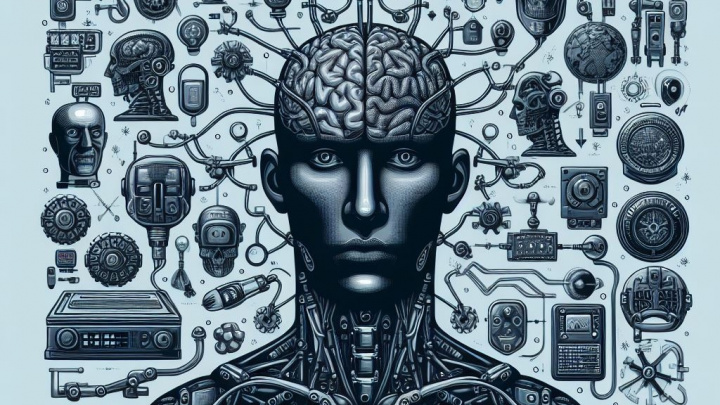接着,其他人开始依次大声说出答案。第一个人给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你觉得很奇怪,心想也许是他看错了。然后第二个人也给出了同样错误的答案。第三个、第四个,以及所有其他人都一样。轮到你回答时,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一致陈述了一个与你亲眼所见明显相悖的结论。你会怎么做?是坚持你所看到的,还是向群体屈服?
这个两难的困境,正是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著名实验的核心。他提出的问题至今仍不过时:群体压力能否凌驾于我们清晰的个人感知之上?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不安。
一场看似无害的视力测试
阿希的实验设计以其简洁而著称。他告诉参与者(均为大学生),他们正在参加一项视力测试。他向他们展示如上所述的线条,并要求他们大声说出答案。
然而,其中的玄机在于,每个小组中只有一名真正的、“不知情的”被试。其余的都是“同谋”——为阿希工作的演员,他们遵循着预先设定的剧本。这位毫无戒心的参与者被故意安排在最后几个回答,迫使他先听完其他人一致的(且故意错误的)意见。
实验共包含18轮,或称“试验”,每一轮都使用一组不同的线条。在最初的几轮试验中,每个人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以建立信任,让情境看起来可信。但在18轮中的12轮“关键试验”里,所有的同谋都给出了同一个公然错误的答案。
内心冲突的时刻
你几乎可以想象出被试脸上的困惑。听到第一个错误答案后,他们可能会笑一笑,以为有人在开玩笑。听到第二个时,眉头就会皱起来。在第三个和第四个错误答案之后,他们最初的信心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和怀疑。“是我有问题吗?我看错角度了?这里面有什么我没搞懂的门道吗?”
参与者会开始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或紧张地笑。房间里的两难困境变得愈发明显:我是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官而冒险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还是应该相信群体而否认我亲眼所见?
惊人的数据结果
阿希的发现至今仍是社会心理学的基石,因为它们揭示了一种深刻的人类倾向。
- 75%的参与者至少有一次屈服于群体压力,给出了明显错误的答案。
- 在所有关键试验中,所有回答里有37%是从众的,即与群体的错误答案一致。
- 作为对比,在一个对照组中,参与者在没有群体压力的情况下私下给出答案,其错误率低于1%。
这一鲜明对比证明,导致错误率急剧上升的并非任务的难度,而完全是来自群体的压力。
为什么?从众心理学
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在实验后的访谈中,阿希确定了两个主要原因:
- 规范性从众(渴望融入群体):大多数给出错误答案的参与者其实知道群体是错的。他们之所以选择从众,是因为害怕被排斥、嘲笑或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他们不想惹是生非。这种渴望归属感的人类天性,被证明比他们陈述事实的决心更强大。
- 信息性从众(寻求正确答案):一小部分参与者则真正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他们想,“如果所有人都看到同样的结果,那错的一定是我。”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群体视为比自己感官更可靠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境中(而群体的一致性恰恰创造了这种情境)。
但让我们退一步思考。为什么这种融入群体、接受群体意见的冲动如此强大?答案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中。千百年来,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群体。
- 作为生存策略的群体心态:一个孤立的早期人类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猎物,且在自然元素面前无能为力。群体意味着保护、安全和更有效的资源采集。一个被群体驱逐的个体,基本上等同于被判了死刑。这种残酷的选择性压力已将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写入了我们的DNA。我们的大脑进化到将社会排斥视为一种真实的、生理上的威胁。当实验中的参与者反对群体时,他们大脑的警报中心可能被激活,就像面对真正危险时一样。
- 群体智慧(或对其的假设):在我们的祖先环境中,群体共识通常携带着关乎生死的信息。如果部落里的每个成员突然都朝一个方向跑,明智之举不是停下来寻找狮子,而是跟着他们一起跑。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没能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下去。这就是“信息性从众”的古老机制:群体的意见成为一种快速、高效且通常可靠的理解世界的捷径(一种启发法)。
因此,在阿希实验中观察到的行为不仅仅是瞬间软弱的标志。它是一种进化的回响——一种深刻、古老的生存本能在现代心理学实验室的无菌墙壁内回荡。
一线希望:一个盟友足矣
阿希并未就此止步。他进行了实验的多种变体,这些变体或许带来了更重要的教训。最有力的结果来自于当他在同谋群体中引入一个“盟友”时——即另一个始终给出正确答案的人。
结果如何?从众率骤降了近75%!只需要另一个人来验证参与者自己的看法,他们就能找到坚持自己真相的勇气。这表明,社会支持是抵抗群体压力的极其有效的解药。
阿希实验的遗产:为何至今仍意义重大
一个关于判断线条长度的1950年代的实验可能看起来很遥远,但它的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试想一下:
- 职场会议:我们有多少次仅仅因为老板和大多数人都支持一个坏主意而点头附和?
- 同伴群体:当朋友们不公正地批评某人时,我们敢于直言不讳吗?
- 社交媒体: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就未经批判性思考地追随潮流或分享观点?
- 历史:这个实验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会出现整个人口都追随明显错误或不道德意识形态的社会现象。
实验的回响:支持者与批评者
如同任何里程碑式的科学研究一样,阿希的从众实验也受到了支持者和批评者的辩论与分析,所有这些都塑造了我们对其研究结果的理解。
支持者
绝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仍然将阿希的研究视为基础。他们的主要论点是,该实验在一个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优雅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压力的力量。它表明,群体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可测量且强大的力量,甚至能够凌驾于基本的感官知觉之上。阿希的发现为其他极具影响力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例如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米尔格拉姆曾是阿希的学生),该实验研究了对权威的服从。
批评的声音
然而,几十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批评,为解读实验结果增添了新的视角。
- 人为设定的环境(生态效度低):最常见的批评是实验室环境过于人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和一群陌生人一起判断线条的长度。实验的风险极低——答错了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批评者认为,当涉及到重要的道德或个人问题时,人们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信念。
- 文化与历史背景:这些实验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进行的,那是一个以冷战偏执和强烈的社会整合文化(麦卡锡时代)为特征的时代。在其他文化(尤其是在更具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中进行的重复研究,通常显示出较低的从众率。相反,在更具集体主义文化(如亚洲)中的研究,则通常发现更高的从众率。这表明,人们屈服于群体压力的程度受到文化的严重影响。
- 过度强调从众行为:一些批评者认为,阿希和他的追随者过于关注从众行为,而对抵抗行为关注不够。我们不要忘记,在关键试验中,近三分之二(63%)的总回答是正确地反抗了群体!人们也可以将结果解读为人类独立性和正直品格强大力量的证明。据报道,阿希本人也对自己实验中抵抗的人数之多感到惊讶。
这些批评并没有否定该实验的根本重要性,但它们提醒我们,人类行为极其复杂,我们必须始终考虑情境、文化和个体因素。
结论
所罗门·阿希的实验并不证明人是意志薄弱的。相反,它揭示了我们是具有深刻社会性的生物,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深受周围人的影响。但它也提醒我们勇气的重要性——那种敢于说出“虽然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但B线才是正确答案”的勇气。
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那25%的人——那些从未,哪怕一次也没有向压力屈服的参与者。他们证明了,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自主和正直也是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