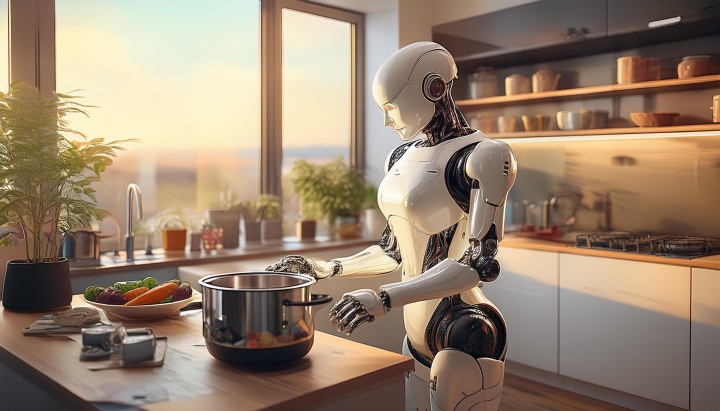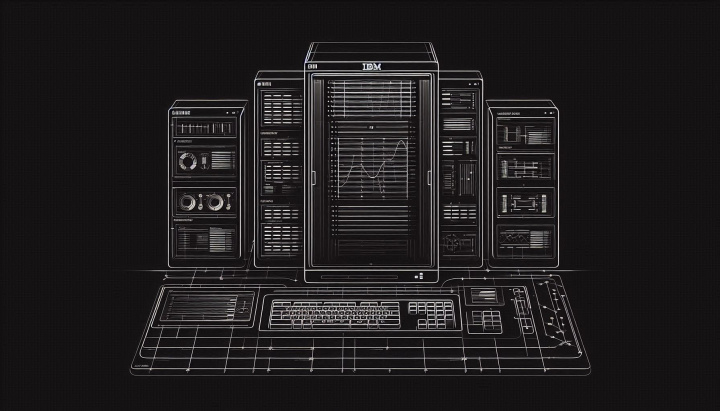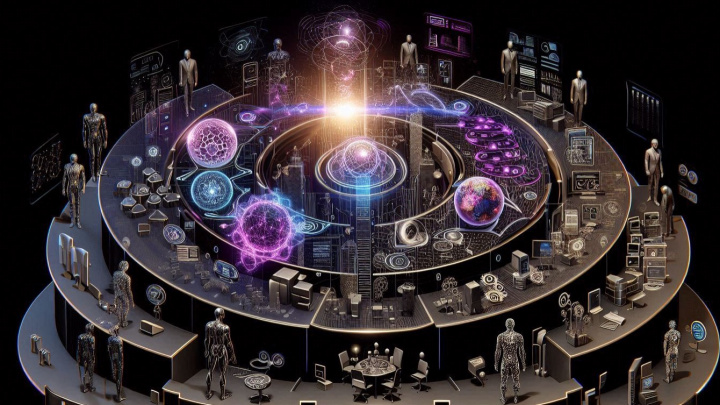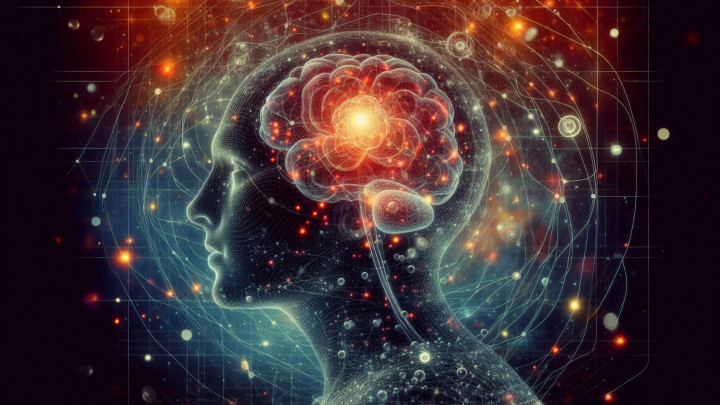我们目前为止讨论过的机制——各种形式的互惠和网络结构——已经展示了合作如何在期望未来回报或社群安全感中产生和维持。但在更大、更匿名的群体中,声誉不那么重要,未来再次相遇的机会也微乎其微,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搭便车问题便会大行其道:即享受公共物品带来的好处,却不为其做出贡献的诱惑。
社会是如何对抗这种极具腐蚀性的力量的呢?瑞士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西蒙·盖希特(Simon Gächter)的开创性实验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我们愿意做出个人牺牲来惩罚自私的人,即便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直接的物质利益。
揭露自私的社会实验:公共物品博弈
费尔和盖希特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们通过一个名为“公共物品博弈”的简单练习,在实验室环境中模拟了搭便车困境。游戏设置如下:
- 一组四个陌生人,每人收到20个货币单位。
- 在每一轮中,每位玩家秘密决定将自己20个单位中的多少投入一个“公共池”。
- 在每一轮结束时,实验者会将池中的总金额乘以一个系数(例如1.6),然后将总和在所有四名玩家中平分,无论他们个人贡献了多少。
逻辑很清晰:对整个群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每个人都贡献出全部20个单位,因为这样可以使集体收益最大化。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最具诱惑力的策略是搭便车:自己什么都不贡献,但仍然可以分得一份他人贡献乘以系数后的收益。实验的第一阶段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可预见的结果:仅仅几轮过后,信任便烟消云散,贡献额骤降至几乎为零。合作彻底瓦解了。
转折:惩罚的力量
接着是实验的第二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阶段。玩家们被赋予了一个新选项:在每轮结束后,看到所有人的贡献额之后,他们可以花自己的钱来惩罚他人。玩家每花1个货币单位用于惩罚,被惩罚的玩家就会被扣除3个单位的收益。
从经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决定似乎纯属非理性。你为什么要花钱去伤害一个你再也不会见到的陌生人,尤其是在惩罚他们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经济收益的情况下?
结果是戏剧性的。玩家们广泛地使用了惩罚选项。他们开始严厉惩罚那些贡献低于团队平均水平的人,尤其是那些完全不作贡献的搭便车者。效果立竿见影:由于害怕受到惩罚,合作水平飙升,并在实验的剩余时间里保持在高位。参与者们自愿地维持了一个代价高昂的执行系统,将公共利益从彻底崩溃的边缘拯救了回来。
为何这种惩罚是“利他”的?
这一现象被称为利他性惩罚,因为从群体的角度来看,惩罚行为是无私的。惩罚者为了惩罚一个规范违反者,承担了个人成本(损失用于惩罚的钱)。从这一个行为中,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个人利益。利益归于整个群体:惩罚的威慑作用稳定了合作规范,在未来的回合中,每个人(包括惩罚者)都将从更高水平的合作中获益。因此,惩罚者是为公共利益做出了个人 sacrifice。
正义的演变及其双刃剑
但究竟是什么驱动了这种行为?研究表明,关键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当我们目睹不公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时,如果我们有机会惩罚作弊者,我们大脑的奖励中枢就会被激活。执行惩罚会让人感觉良好,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正义感。很可能,早期人类群体中那些拥有这种“无私执行者”的部落,在维持内部秩序与合作方面远比那些完全由自私个体组成的部落更有效,从而获得了演化优势。
这种机制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当我们纳税时,我们共同资助了警察和司法系统——这正是同一种现象的制度化形式。但它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持续运作:社会舆论的谴责、流言蜚语、公开羞辱,甚至现代现象如“网络公审”(cancel culture)的某些方面,都可以被解释为利他性惩罚的表现形式。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机制是一把双刃剑。维护公正合作规范的力量,同样可以被用来强制执行专断、排外或压迫性的规范。同辈压力、对循规蹈矩的要求以及对“异见者”的惩罚,都源于同一种本能。机制本身是中性的,其力量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完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规范的道德品质。
结论:合作的坚定守护者
利他性惩罚的发现揭示了,人类的合作并不仅仅建立在精于计算的自身利益或被动的结构优势之上。我们拥有一种主动的、充满情感的本能,驱使我们去守护社群的规范,并惩罚那些违反规范的人,即便需要付出个人代价。这种倾向,尽管有时看起来非理性且代价高昂,但实际上是让我们能够在庞大的陌生人群体中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它是合作的强大——但有时盲目——的守护者,没有它,我们的社会将脆弱得多。